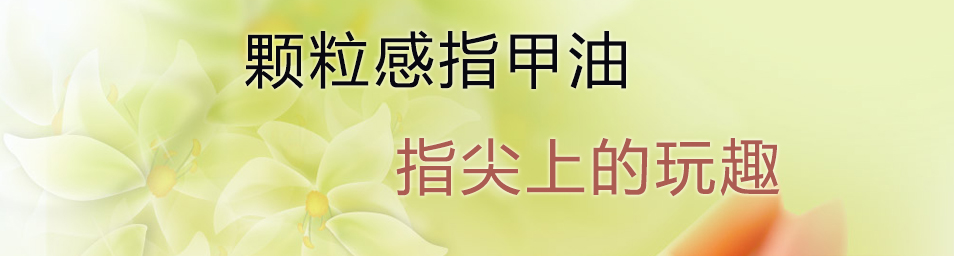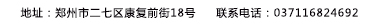|
《金阁寺》跟西方小说有一个共性,它也可以用一句“谬论”来概括:前途无量的金阁寺弟子亲手烧毁了金阁。 小说从开始到结束就是论证这个命题是如何一步步成立的。天生结巴的小和尚沟口从起初对金阁的崇敬和向往,经过与现实世界的摩擦,最后演变为不得不烧毁金阁来拆除自己与世界沟通的障碍。小说里还有许多诸如美与丑、认识与行动等哲学论辩,其思想性并不是单一的。金阁寺从物质性的建筑物最终上升到一种抽象的美和崇高,这种美与崇高又能不能在庸俗的现实世界里毫不变质呢。小说还进一步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思考战后日本的生存方式和意识。 小说的结构十分工整,一共十个章节,每个章节情节十分明晰,行文简洁,扎实地论证了沟口是如何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小和尚转变为一个纵火犯的。 在引入沟口心中的金阁寺时,作者设置了一个巧妙的转换,从夕阳下的小山想到金屏风,然后突然提到金阁寺。看似突兀,实则是有过渡的。夕照下的小山跟金阁寺都是金色的,在视觉上相似;小山遮挡了大海,金阁阻碍了我与世界的沟通。 沟口的结巴具有明显的寓意,跟小说后面提到的龋齿是同一类的东西,是一种阻碍,跟金阁也有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章里,少年英雄出场时,沟口在花团锦簇的崇拜场面之外,唯一与英雄的对话却出乎意料地通畅;这个细节看似有悖于设定,实际上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沟口通畅地说出口的话是一句拒绝的话,他说:“不,我要去当和尚!”是拒绝与外界沟通的姿态。沟口用铅笔刀在英雄的剑鞘上划下三道刀痕,这明显是他之后烧毁金阁的预演,这种艺术手法其实在生活中也能观察到,比如人们常说的“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如果是学习写作,感知艺术手法最好的方式还是从生活中去体会。 有为子跟沟口的关系基本奠定了后来他一系列行为的基础。沟口渴望有为子的身体,但又无法与她正常沟通,他自己反倒成了她骑车上学道路上的阻碍,将自己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她面前。有为子背叛情郎,使她的美下降了,沟口以为她属于他了;而随后有为子的死,是希腊悲剧式的,她的美再次升华了。 可以看到,有为子跟金阁也是有呼应关系的。战后的日本,屈从于美国人制定的宪法,旧日的日本传统精神消失了,就如同金阁每天都在被游人的观赏,金阁的美在庸常的世俗里苟延残喘。在作者或者沟口心中,与其如此,还不如毁灭它,让它在物质层面消失,在精神层面永存,成为一出真正的希腊式的悲剧。毁灭的瞬间也是它的美最为耀眼的时刻。 少年鹤川的出场很特别,“一个身穿白衬衣的少年横躺在草地上”,“早晨从树叶隙间筛落下来的阳光,把青草的淡绿色的影子撒满了大地”,类似这种段落,把整个环境烘托的那么美好,实际上作者要表现的是少年鹤川的阳光的一面。 鹤川跟沟口是完全相反的一类人,他口齿伶俐,善于与人沟通,非常阳光,他把沟口阴暗的感情一一译成明朗的感情,他是一个透明的结构体,是一种光明的力量。他给沟口提供了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暂且称之为“鹤川方式”,就是用明媚的力量来与外界和谐相处,化解心中的阴暗。有鹤川在身边,沟口感到与外界相处愉快。 然而,这一时期沟口之所以可以跟金阁靠得最近,并沉湎在它的美之中,还因为金阁随时处于被美军轰炸的危险之中。在三岛的美学里,美会给人压抑感,在美的面前,自己会变得渺小,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但是当金阁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它就下降到与沟口一样的高度,他可以无所畏惧地去爱它,“烧毁我的火,也定会烧毁金阁”,金阁看似那么的坚不可摧,却原来跟“我”一样拥有易燃的碳素肉体,于是金阁的美对“我”没有威胁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更靠近了。 烧毁我的火,也定会烧毁金阁。这种想法几乎陶醉了我。在遭受相同灾难、相同不吉利的火的命运中,金阁和我所居住的世界一元化了。尽管金阁坚固,却与我的脆弱而丑陋的肉体一样,拥有易燃的碳素的肉体。这么一想,我似乎可以把金阁藏在我的肉体里,藏在我的组织里,然后潜逃,就像潜逃的盗贼把昂贵的宝石咽下,然后隐匿起来似的。 ——《金阁寺》节选 关于美的压抑感在现实生活确实存在的,我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下。我曾经在一个宴会场合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她整个人非常的耀眼。我记得那天她穿白衣服白裙子,个子高挑,长发及腰,就像一条光带在人群中飘来离去,接待宾客送上的礼物,她姿势优雅,笑意盈盈。我的眼睛忍不住去追踪她的身影,可一旦她靠近我,想跟我说话,我就不自觉地后退,所以显得很怂的样子。认识美女当然是有愉悦感的,可是更多是自惭形秽,你会想到,她那么美,那么耀眼,她的存在越是确凿,我的存在越是可疑。所以那天晚上我乘地铁回家时心里是很复杂的。奇怪的是,刚刚离开我就记不起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明眸酷齿,脸上的妆容没有一点瑕疵,可是具体的五官模样竟然想不起来,我越是使劲回忆,记忆就越是模糊,本来是实体的美很快就变成想象中的美,她的美在我的头脑中升华了。我忘记了她,也铭记着她。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年后。当我再次见到她,是在非常杂乱的街道上,她驾驶一辆大号的奥迪车,里面有四排座位的那种。随后我上车,近距离看见了她,再次震惊了。我看见她穿了一身颜色暗沉的衣服,大得不合身,牛仔裤估计三四天没洗了,运动鞋上面还有泥泞斑点;我还看见她握住方向盘的双手显得很粗糙,指甲缝里甚至有点灰尘;我看见她的侧脸并不光洁,发际线一带是有色斑的,她转头过来说话,我惊讶地看见她额头上的皱纹。我实在无法想象,这就是一年以来我心目那个女神形象的本人,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可是我看见她这个样子心里反而是没有压力了,变得健谈了,变得自信了。我这种心理的转变就是来自于我看见了她的美的背后是跟我同样平庸易朽的肉体,所以我们的关系反而变得靠近了。 在第二章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沟口跟鹤川在天授庵看见一个军人跟他的妻子告别的场面。因为这个军人的妻子没有写她名字,我们就暂且称她为“军嫂”。军嫂长得很像有为子,在沟口的心中,她就是有为子的复活。自从有为子死后,她的美永恒地遗留在沟口的心里,那种悲剧性的壮烈之美,也是作者三岛由纪夫所追求的。可是“军嫂”这个角色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有为子的复活?我们注意看,这段情节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沟口等待金阁被空袭的愿望逐渐落空的时候,出现在他和鹤川游完南禅寺,观赏寺庙墙壁上精美的壁画之后。眼看即将毁灭的金阁复活了,但是复活之后的金阁再也不是从前的金阁,它从此将与邪恶的世俗同流合污;就如同日本在投降后没有被吞并被瓜分,日本似乎依然还是日本,但却永远背负非正常国家的污名;有为子也复活了,那么美的女子活过来了,但是她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恶心的动作,掏出莹白的乳房,挤出乳汁,让军人丈夫就着茶水喝下去。曾经称霸亚洲、远征美国、嗜血成性的日本军人居然喝下了女人的乳汁,变成羸弱的婴儿,不得不说,这是三岛由纪夫对日本不能拥有军队的现实的绝望! 在第三章里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地方。一个是“南泉斩猫”的典故,一只猫引起相堂相争,南泉和尚选择挥刀斩断猫首,其弟子赵州则选择头顶草鞋的宽容。猫,相争的美,当美成为阻碍,成为矛盾,就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南泉和尚的“杀人刀”,一种是赵州的“活人剑”。在小说中,鹤川与“活人剑”,柏木与“杀人刀”,都有呼应关系。每个人都会在这二者之中必选其一。巧妙的是,这个典故出现在日本战败、金阁确定不会被轰炸的时候,说明这个时候金阁也变成了某种阻碍、某种矛盾。在写作中,情节的先后顺序是如此的重要,会直接影响文本的意义指向。 那么沟口会选择哪种方式呢?他认识了鹤川,这个阳光少年曾带给他对生活的愉悦体验。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与一切都隔绝了,金阁重新以永恒地姿态出现他的生活中,威胁他的存在,成为他的阻碍。俗世中的人们以生活和行动来体验罪恶,他想沉浸在内心的罪恶之中;鹤川没有办法帮他,他跟他不同,他没有他的野心,他生命纯洁的末端正在燃烧,未来只留下纯洁和污垢。沟口内心的邪恶终于暴露出行动的企图,在美国军官的命令下,他踩踏了孕妇的腹部,将一个生命提前扼杀,他却从中获得了某种罪恶的快感。 一只蹬着瘦长的高跟鞋的脚,伸到吉普车的踏板上。这么寒冷,竟不穿袜子,我惊愕万状。一眼就可以辨出这女人是以外国兵为对象的娼妇,她身穿殷红的大衣,脚趾甲、手指甲都染上了同样殷红的指甲油;大衣下摆松开时,露出了肮脏的毛巾睡衣。这女人也酩酊大醉,眼目发呆。那男人倒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看样子,女子是刚起床,抓去大衣被在睡衣上,围上围巾就出门来了。 ——《金阁寺》节选 踩踏孕妇的场景发生在雪后天晴的环境里,万物银装素裹,雪中的金阁美轮美奂,变得与世无争,变成画中的金阁。这个时候,美国大兵带着怀孕的女子出现在金阁前,要注意到女子身披殷红大衣,手指甲脚趾甲都涂上同样殷红的指甲油,脸色苍白,涂着绯红色的口红。如此密集又醒目的红色出现在雪地里,有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白里透红”,既美,又残忍。香港电影经常使用这一招,为了突出暴力的残忍性,导演们喜欢往白色的道具上喷洒血浆,无论是枪战片还是武侠片,白衬衣、白墙壁、窗户纸等道具就是为了喷洒血浆而出现的。连昆汀都学到了这一招,在《被解放的姜戈》里血浆洒在棉花上,用的也是“白里透红”的艺术效果。所以当我们听到有同学对万柳二区楼底墙壁上的在白体恤上用红墨水作画的装饰品表示有恐怖的反感时也就是不足为奇了。另外,孕妇在雪地里流产或分娩也是小说家们常用的桥段。《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雪地里出生的,当郭靖的母亲半夜在大漠雪地里生下孩子,月亮的清辉洒满大地,她把婴儿从胯下举起来,用牙齿咬断脐带。我对那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想一想,郭靖的母亲在月光下从莹白的雪地里举起沾满血污的婴儿,咬断脐带。一种对于生命的崇敬感油然而生。可是,雪地里流产却是残忍的,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最后一个场景,筱燕秋孤独地在剧院外的雪地里挥舞水袖,唱她的《嫦娥》,因为吃过打胎药,一滴滴的血就从她的身上落到雪地里,嫦娥在往天上飞,她却在往下坠落,人物的悲剧命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艺术呈现。 沟口就是在这样一种残酷的行为里释放了他内心被压抑的邪恶,成为他一步步走向堕落,走向纵火犯的转折点。 第四章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柏木。沟口跟柏木的相遇可谓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他们都是有残疾的,沟口是结巴,柏木有一双X型腿,都是不被外界接受的,是美的反面。柏木觉得残疾人与世界之间不应该追求和解与融洽,不用消灭对立状态,而是以全面承认对立状态的形式出现,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好好利用自己的X型腿,残疾成为他存在的条件。柏木失去童贞的故事就可以体现他这种观点。美貌的小姐姐主动示爱,他坚决拒绝,因为他拒绝美为了获取自己存在的自尊而公然欺凌于丑陋之上,丑陋也有自尊;只有当他面对丑陋的老妇人时才会有性欲的快感,更重要的是,老妇人对他的X型腿有着虔诚的崇拜。于是,柏木就给沟口提供了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柏木方式”,就是承认美与丑的对立状态,去玷污美,摧毁崇高,以此取得丑的或者邪恶的存在空间。在柏木阴暗的哲学里,关于美与丑的认知让人瞠目结舌,他说丑陋、血腥能让人变得纤细,而美会让人变得残忍,人类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的。 对于沟口而言,“柏木方式”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他疏远了鹤川,不信任“鹤川方式”。然而,金阁的美依然在发挥它巨大的威力,在第五章里沟口两次接近异性都是临阵脱逃,金阁在用它那永恒的美告诉他,他面前的女子不过一具易朽坏的、终将会被蛆虫和蝇蚊围绕的肉体。金阁是横亘在沟口与异性之间、与世界之间的阻碍,使得沟口无法释放内心的欲望。他跟金阁是对立的,可是金阁的威力是那么的巨大,他无法战胜它,用“柏木方式”也无法克服;与此同时,沟口收到了鹤川的死讯,那么少年是那么的纯洁与无垢,但有是那么的脆弱。鹤川曾经用他伶俐的口齿和宽容的心态为沟口筑起一架通向世界的桥梁,尽管鹤川并不完全了解他,但是那座桥梁依然是有效的。现在,“柏木方式”的不可行,“鹤川方式”又失去了,沟口与金阁之间陷入了拉锯战。 转机出现在第六章,一年以后,柏木带着尺八出现,发表了一通关于艺术的哲学探讨。他讨厌文学,讨厌建筑,因为它们总是追求永恒,只有音乐,追求瞬间的美,一曲终了,美立刻飘散无形。柏木还发表了自己对于“南泉斩猫”的看法,他说美是龋齿,必须拔掉,猫就是一种美,当这种美引起争执的时候,它就是龋齿,南泉和尚挥刀斩猫,就是拔掉龋齿。 这一次,沟口算是承认了“柏木方式”,并再次运用它。在柏木的引荐下,“军嫂”——或者说复活的有为子——以插花师傅的身份出现了,沟口一直以来就渴望着有为子的身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他依然失败了。金阁再次阻碍了他。他与金阁之间已经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他要制服金阁。 第七章里沟口与老师道洤和尚的矛盾升级,使他失去了拥有金阁的可能性。他无法拥有金阁,金阁却在掌控他。于是他借钱出走。 这一章的末尾有一段舞鹤岗的风景描写。作者将沟口的内心转变通过外化的风景表现出来,最终确立了烧毁金阁的决心。 这里正是日本的海啊!是我所有的不幸和灰暗思想的源泉、我一切丑陋和力量的源泉。海,波涛汹涌。海涛后浪推前浪地接踵而来,前浪与后浪之间可以窥见通畅的灰色深渊。昏暗的海面上空,密密层层的积云既凝重又纤细。无境界的凝重的积云不断地镶嵌着无比轻盈而冰冷的羽毛般的花边,围着中央隐约可见的淡蓝的天空。铅色的海,又背靠着黑紫色的海角上的群山。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动摇和不动。不断活动着的黑暗力量和像矿物似地凝结了的感觉。 ——《金阁寺》节选 以上节选只是其中一个段落,我觉得沟口出走去寻找大海的过程是很值得反复阅读的,他的心理描写非常独到,值得我们学习。前面也说过,沟口小时候住的至乐村,大海被一座屏风一样的小山遮挡了,但风一吹,就有海的气息,当地就叫“海的预感”。在这里,大海是有象征含义的,沟口走过何川、走过原野,终于抵达了海边,这是他内心克服障碍,直面自己内心欲望的过程。所以他要烧毁金阁,拆除障碍。 沟口在头脑中进行着对永恒与短暂的思辨。他认为金阁看似不朽,可只要一点火源,就能彻底毁灭;而人看似极易朽坏,可是基因的代代相传,却能真正抵达永恒。于是在他心中,金阁的永恒之美跌落了。他以为他发现了世界的规则和意义,如果烧掉金阁就能把这种世界的意义传达给人们。烧毁金阁的念头取得了正义性。 沟口被警察遣送回寺,见识了母亲的丑陋,遭遇柏木的索债,他变得更加的孤独。就在此时,鹤川死前的信件披露他曾经跟柏木很要好,甚至很多事只对柏木说,没有跟沟口提起。这让沟口很伤心,之前他还怀念着鹤川,但是鹤川的自杀真相让“鹤川方式”变得彻底无效。两条道路,只剩下一条了。 然而,就在此时,小说的写作再次营造了起伏。柏木认为改变世界的是认识而不是行动,这对沟口来说是有影响的,尽管他口上不承认。 所以在第九章里沟口选择了在妓院里彻底的堕落,期待老师把他驱逐出寺,但是老师总是以恩惠代替垂训,对于沟口的行为总是无动于衷。 在这一章的最后,有一段很精彩的心理描写。沟口看见老师卷曲在地上,以非常卑微、痛苦的姿势诵经。沟口的内心起了两层斗争,第一层是他觉得老师生病,想要去扶他起来,但又担心如此过来老师会感谢他,从而削弱他烧金阁的决心;第二层是联想到老师是位高僧,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很感动,但又立马想到,他是做给他看的,是伪善的,告诫自己不要上当。这是人物内心的波澜,如果写得好,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常常有两种感受力,甚至更多,有直觉的,有根据经验判断的,这些内心活动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自我,其实很难分清。无论怎样,沟口选择了拒绝感动而倾向罪恶,他觉得自己跟老师是两个世界的居民,他是自由的,已经不用考虑老师的感受了。 沟口万事俱备,准备与金阁同归于尽。 他朝朝暮暮思念的金阁,最终没有希望当上主持拥有它,屡屡阻碍他接近异性的金阁,他最终决定以毁灭的方式制服它,然后把它完全地收归于自己的体内。 实施纵火的过程也并非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作者显示出高超的节奏把控能力。在这最后一章,他竟然加入了新人物:禅海和尚。禅海和尚不同于沟口父亲的懦弱和道洤和尚的肉欲,他豪放、坦荡、慈祥、朴素,更重要的是,沟口觉得他理解他。在禅海和尚面前,他完全地、一无遗漏地被理解了,而且禅海和尚也并没有阻止他,于是沟口就有了行动的勇气。 就在放火的前一刻,他又犹豫了,那就是行动的意义何在,柏木说改变世界的是认识,既然自己已经在头脑中烧毁了金阁,又何必多此一举真要付诸行动呢?可是沟口立马就认定这也是他行动的阻碍,按照《临济录》的说法,“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家眷杀家眷,始得解脱。”要用行动去解脱。这就是沟口在纵火前的心理变化。而在纵火成功之后,他却临时改变了同归于尽的想法,转向寻求生,他要活下去。看来,只有毁灭金阁,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与金阁的对抗的过程中取得胜利。 《金阁寺》写得非常的工整,每一章节的内容都恰到好处。 小说中有多重呼应关系值得一提。 南泉和尚——猫——赵州 柏木——美(阻碍)——鹤川 沟口——金阁(结巴、龋齿)——沟口 死去的有为子——复活的有为子 行将毁灭的金阁——不被轰炸的金阁 传统的日本——战后的日本 公子岳赞赏 人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