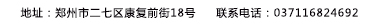|
走那么远的路,想必也饿了吧。 故事爆炸机,一心喂饱你。 刘丹青/图片 前言:好久不见~~《流星花园》今年3月23日杀青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疲惫。将近一年的剧本创作,让我觉得自己不断在消耗而没有实质性的输入。所以这段时间,我以平均两天一本书的速度在阅读各领域的书籍,同时也创作了这篇一万三千字左右的小说《防狼小队》。 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我一直试图挖掘个体本身。为什么两种相互矛盾的特质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些特质又是如何影响这个人与周围的人、与世界的相处?为什么两个人追求一样的东西,最后却得到相反的结局?为什么两个人分别以务实和务虚的方式生活,结果又殊途同归?到底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好的?我们又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获得哪些好处,付出哪些代价? 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不断去探讨的。虽然小说还存在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尚浅的阅历、不成熟的写作技巧,但我已努力走近小说里的三个女生,也努力去追问人性的真相。 文章较长,祝阅读愉快!希望能在未来为大家写出更好的小说O(∩_∩)O (强调:小说为虚构,并不是真实故事。) 第一次跨进大学校门时,我反复警告自己,不要和任何一个人走得太近。萍水相逢、擦肩而过,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用心。 大人没教过,书的字缝里也没写过,凭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好像必须得这么做。从小到大,认识的人都说我是上黑板的乖乖女,规矩,听话,又因为太懂事而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 其实他们不懂,一个跟着直觉走的人是最叛逆的。 梦娇和争争当然也看不出来。舍友四年,梦娇一直叫梦娇,争争本来叫真真。家人的心愿浓缩在两三个字上,是光环,也是一辈子的镣铐。过来人都小心眼,不说为心愿付出的代价有多痛。 那年我从江南去大西北读书,高铁还没停站,一身的水已被榨干。我拖着箱子,在宿舍门边喘气,想进,脚又怕生。眼前,梦娇爸爸已帮她收拾好一切,腆着啤酒肚,一副官腔的笑很扎眼。本地人就是方便,开车方便,回家方便,走后门也方便。 梦娇坐桌边,正愁怎么摆一堆毛绒公仔。拿上柜又拿下来,也许更愁的是把自己摆在哪儿。 梦娇自恋,不舍得每个被注视的机会。很快,她的眼神划过来,在我身上划出一道伤口。瞬间,我感到她在眼神里对我做出了判断——这个女孩比较次,做事不用看她的脸色。 不过,梦娇多少有点脑子,从大人那偷学也记得学全套。下一秒,她就收起这眼神。“舍友你好呀,我叫梦娇,梦幻的梦,娇贵的娇。”语气里似乎很得意这个名字,或者说自己拥有的一切。梦娇把其他女生当男生看。 后来,争争也这么介绍:我叫许真真,真实的真,真诚的真,和你们一样,都是社会学专业的。梦娇一听反问道,咋不是仿真的真?此刻争争的笑只给到一半,放出去也不是,收回来也不是。好在她是一个行动先于思想的人,脑子还没琢磨完这句话,嘴抢先一步:都是一个字,没啥区别! 宿舍里四张床三个人。这下放心了,梦娇算老大。 和梦娇一样,争争也是西安人。但两个西安又不是一个西安,起码梦娇是这么认为的。她倒没问争争从哪个城中村出来,反正一碗羊肉泡馍,有人是羊肉,有人是馍,有人连汤头都算不上。 争争的笨在脸上,手脚却很灵活。铺床,擦桌,端一盆水擦地时,像在村口捧一碗油泼面。农活做多的样子,却显得脸上更笨了。当然,人再笨,也能分清起码的优劣。她有事没事地找我说话,眼神却偷瞄向梦娇。仿佛钓鱼,却没有诱饵,只能干着急地抛一根竿。 忽然我感到一阵恶心。争争真心实意的示好,让我觉得自己和她一样卑陋。 在西安读大学,说不上好,也不算坏,有种命该如此的平静。反正去哪都有得有失,做什么都可喜可悲。我惊讶于自己的冷漠,以及一种还没长大、就已衰老的悲凉。想这些的时候,争争正冲着食堂窗口的大妈喊:“浆水鱼鱼!大碗!”她扑腾扑腾地,声音假装鲤鱼跃龙门。 才知道浆水鱼鱼不是鱼。不是所有年纪增长的人都会长大。 不锈钢盆里,油腻腻的鱼晃着。分不清肚皮还是背脊,分不清活的还是尸体。“玉米面做的,老陕小吃,你肯定没吃过!”争争说的时候,十几条鱼游进她嘴里。 好像电影里结婚摆宴席的画面,端上来的也不是活鱼,是“摆着是个意思”的木鱼。不用来吃,用来看。哦想起来是陈凯歌的《黄土地》。陕北农村,信天游,干裂的土地浑浊的黄河,争争的两坨高原红就这么被吹出来了。 想问她有没有看过,但又缝上嘴。不是文艺青年犯不着显摆,再说争争应该也没看过。 争争把一大碗浆水鱼鱼解决了,连汤都没剩。她吃力地呕一个饱嗝,指着我的碗问,咋还剩这么多,不好吃吗。我摇头,好吃,但我吃不下了。她可惜地摇头,你们南方人的胃就是小。 不是胃小,是克制。我习惯性地把这句话在心里舔一遍,咽下去。那时起,我就知道争争是用力过猛的人,一个肉夹馍足以吃饱,她嘴馋,偏要吃两个。 第一次吃浆水鱼鱼时,还没正式开学。黑压压三千多人,穿着军装,分到校园各地踢正步。军训是高中和大学的无缝对接。脚离地面25厘米是诗词默写,实弹射击是命题作文,黑脸教官是批卷老师。那时还没人逃课,没人敢对统一标准说一个“不”。 不喜欢,但依然按部就班地做。争争更是咬牙,力气全绷在踢出去的腿上。想起她刚进这学校的激动,好像努力过头中了彩票。能坚信种一颗种子得一朵花的人是幸福的,我羡慕争争,因为我常觉得种一颗种子,仅仅是种一颗种子。 那时大家都在暗中较劲,想争第一排的位置,最后大检阅时被首长一眼看见。 夜深在床上,听着争争汗水浸过的熟睡声,我总在想站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差别。加不了学分,拿不了奖学金,只是优人一等的感觉吗?首长要看那么多连队的那么多第一排,批发市场里摆好的帽子,遮得一张脸都看不清,究竟是在争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几近失眠。 要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军训只是一种模拟练习。出国镀金和家乡土著,自己的男朋友和别人的男朋友,婚礼的排场和孩子的成绩,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比较而不知为何比较。 等到某天早上,争争用二十出头的防晒霜涂高原红、梦娇挤着上千的精华液敷一条象腿时,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可信的理由:或许争争喜欢上教官了。 喜欢说一不二的脸,喜欢有棱有角的威严,喜欢被叫到队伍前做示范的感觉,喜欢他可能给的一点特权。 但争争真的不太懂规则。那晚中场休息,教官卸下脸,问累了一天,谁能表演个节目轻松轻松。刚散架的骨头又僵成木偶,大家望着彼此,一动不动。熬过尴尬的半分钟,梦娇站了起来。几乎是沐着所有眼睛的光辉,她忸怩又不忸怩地笑,要不我唱个歌吧。 当所有人连同教官,一起帮梦娇拍手打节奏时,我在想,她可真会啊。这话要早半分钟,就也没欲扬先抑的效果了。不是唱得多好,是每个人都松了口气,终于有人救场了,终于不会被点名了。 梦娇唱完,有些人也壮了胆,陆续站出来。教官很满意,一切几乎都是梦娇的功劳了。 “教官,你鞋带散了!”梦娇趁热打铁地喊了一句。教官低头一看,压根没散。但他不怒,表情里反倒多了份宠溺,这小女孩太皮了,还真拿她没办法。 第二天训练,教官有意无意地在梦娇身边打转。他盯着时,她比谁都咬牙。一背过身,她就从内而外地瘫了。争争望着教官望着梦娇,大概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偷懒,什么叫偷懒比努力还有用。 军训结束后,争争失落了好一阵。不知是因为教官走了,还是教官给梦娇太多北京哪家医院看白癜风北京那家医院治白癜风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