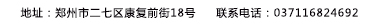|
鲁斯·博恩哈德(RuthBernhard)《盒中(IntheBox)》年 公开的身体,私密的身体 能让他人看到的部分和不能让他人看到部分,应该是人身体上最重要的分割,也就是衣服和外露皮肤的分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露出脸和手脚的一部分已经被完全接纳。这么说的话,脸和手脚属于身体公开的一部分,而与生殖与排泄相关以及其周边的部分属于身体私密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分界下,各种各样的故事开始在身体的表面展开。 在说到身体的隐藏和露出,法国的精神科医生勒莫恩(EugénieLemoine-Luccioni)认为,脸总是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玩捉迷藏:“用衣服遮蔽身体,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把交流的优先权交给脸,但是其实也让身体同时成为了交流的道具。”就像是在暗黑舞踏(——译者注:暗黑舞踏:现代舞的一种,由日本于二战后所创,其舞者通常全身赤裸涂满白粉。)中涂满白粉的浓妆一样,虽然抹去了脸部的信息,但却通过身体的运动同样起到了交流的作用。在像这样通过身体来交流的艺术中,哑剧里小丑无表情的化妆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女性日常的化妆时而浓时而淡,也是希望借此来调节她们在他人心中自己形象的轻重。 直接在皮肤表面的分割也能带来跟这些很不一样的效果。当人涂上红色口红的时候,鲜艳而湿润的红唇立马就以一个独立的形象在脸上凸显出来。这种分离与独立将人带入到多种多样的联想关系中,比如说性器官等等。 雷尼·马格利特(RenéMagritte)这位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在他的画作《Leviol(凌辱)》(年)中画了一副人像。画中人以乳头为眼睛,肚脐为鼻子,性器官为嘴巴,整张脸由一个女性身体的正面组成。而在用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译者注: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的《Qu’est-cequelesurréalisme?(超现实主义是什么?)》(年)封面上,嘴的部分加上了胡子(阴毛)。英文的“Lip(嘴唇)”和日语的“嘴”所指的意思其实不是太相同。日语中“嘴”说的是嘴唇及其周围的部分,所以有“他嘴上长了胡子”这种说法。而画上红唇,就这么把“嘴唇”从“嘴”上分离了出来。 雷尼·马格利特《Leviol(凌辱)》年 雷尼·马格利特为安德烈·布勒东《Quest-cequelesurréalisme?(超现实主义是什么?)》创作的封面年 “恶心”的感觉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中分割和划界有着重要的意义,时尚则将这种意义用更加象征性的手法表现出来。而这种行为又不仅仅限于时尚,它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无处不在。 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分类:东西分为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人分为男人和女人,尽管在外型上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却在服装和行为上被我们加上了过度明确的区分。比如说腿在构造上男女之间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区别,却有着男人穿裤子、女人穿裙子这样的观念。就连乳房没有发育的小女孩都会在游泳的时候穿上连体泳装,可见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固定观念是多么强大。 除此之外还有活着的和死了的,可以吃的和不能吃的,伙伴和敌人,可知的和未知的,有害的和无害的......数也数不清。总之我们总将这个世界一分为二,然后选择其中的一方。 在我们能体会到的各种感觉中,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叫“恶心”。呕吐物、大小便、痰、垃圾、澡盆里浮起的污垢、床单上的头发......这些东西往往会给很多人带来恶心的感觉。我曾经在一所护士学校中教过哲学,有一次我问同学们,什么东西让他们感到最恶心,结果学生们竟然说“怪大叔”。我当时完全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措手不及到差点晕倒,那天的课也不了了之。而说到呕吐物、大小便、痰、鼻涕、口水、污垢、头皮屑等等这些让人觉得“恶心”的东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本来都不是恶心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个歪理,但是仔细想想,呕吐物、排泄物也好,痰、鼻涕或是口水也好,它们最初都来自于身体内部。当他们还在体内的时候,谁也不会觉得它们恶心。如果大小便真的恶心的话,那我们就得无时不刻地服泻药、跑厕所,保证它们不在体内。污垢和头皮屑这些在作为皮肤一部分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恶心,可是一旦从皮肤上脱落下来就变成了“恶心”的东西。而口水的话,恋人或是家人之间相互亲吻也从来没有人会说恶心。这样一来,大小便也好,痰也好,鼻涕也好,口水也好,其实都不是恶心的东西,而是在被设定的某种情况之下变成了“恶心”的东西。 那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存在体内的东西通过身体的开口排出体外的时候,以及身体的一部分从身体上剥落的时候。拿鼻涕举个例子:流鼻涕的时候用纸巾擦掉然后扔进垃圾箱里就没问题,但是让它这么流出来不管就成了问题。大便也是这样,排便后马上冲水,把屁股擦干净就没事。从体内排出的东西,只要能抚去,扔在看不见的地方,就不是个问题。只有这个在中间的情况,也就是“排出”这个状态,或是“进进出出”的状态,才是个问题。 而当界限模糊的时候,或者说里外不分,你我不明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产生“恶心”的感觉。将自己的内部和外部,“自己”和“不是自己”之间的界限变模糊就是所谓的“恶心”。 “界限”这个问题 讨厌和害怕,这两种感觉,在构造上其实相似: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禁忌。拿吃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周围基本上不存在不能吃的东西,但是总有那些没有办法吃的东西。 在哺乳动物中,像牛、羊、猪这样的家畜,多数人都可以毫无问题地吃掉,但是像猫狗这样的宠物就没办法,即使连想都没想过。更别说像是随便吃掉旁边一个人这样恐怖的事情了。就算是被人强迫要吃,也没法吃得下去。和人比较像的猴子,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下得了嘴。对许多人来说,多数家畜类型的动物虽然可以无忧无虑地吃掉,但是其中的鹿、熊或是兔子这样可爱的动物却又被人怜爱。然后远对于像犀牛、长颈鹿这样远在异国的野生动物,或者生活在我们看不见地方的蛇和蝾螈,人们还是难免会有抗拒的心理。可是仔细想想,在这些动物里,没有一个是不能吃的,有的却真的让人没办法吃。这深藏其中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再举一个例子吧:性接触(或是结婚)的禁忌。在现代很多社会中允许自由的性接触,只要是在同一个村落和不同家族的人之间进行就可以。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之间的性接触或者通婚往往是被禁止的。有的地区不允许表亲之间通婚,有的地区可以。同性之间的性接触在长久以来都被视为异类。和所属共同体之外的人,比如说异国或者他族的人之间的婚姻,在以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我们都以“地球人”自居,像这样各式各样的禁忌逐渐被解开。若在这个时代除了近亲通婚之外的禁忌,只剩下和外星人、非生物之间的性接触了吧。把人类看作一个共同体(其实人们经历了长久的时间才意识到,人类其实是一个跨越人种、民族等等的一个概念。),和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存在之间的性接触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禁忌。 是吃东西也好,性接触也好,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会被禁止:当对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一部分,或是家族一员的时候;当对象来自于完全的外部,对于自己是异界存在的时候。后一种情况,由于其来源,大概是因为无法将它置于自己的生活之中,所以让人觉得不舒服;前一种情况,像吃家人或宠物,与其发生性关系等等,大概和“恶心”和“可怕”这样的感觉一样,都是因为对象是来自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人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区别,是一个矗立在分界线上的存在,一个无法分类的存在,所以才会激起我们心中强烈的情感。 如果这些存在被认同的话,意义的差异和秩序就无法成立,秩序的根基也会产生动摇。人们在连续的存在里,用“意义”这个不连续的存在进行分割,利用差异这个体系创造秩序。男/女,成人/儿童,内部/外部,自己/非自己,亲人/他人,正常/异常,能吃/不能吃,有害/无害……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设定出这样那样的区别,附上不同意义,利用这个体系来给予生活一定的安心感。所以对于任何企图破坏这个体系的意图也会特别敏感。为了保护自己,那些模糊界限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或是带有侵略性的东西都会渐渐被除掉。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禁忌。 “感情”这个制度 最要命的是,对于人来说,所有的禁忌,往往正是最具诱惑力的东西。界限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们人为创造的。“天塌下来”的预感、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着极大的魅力。小时候我们老喜欢在烂泥里打滚,即使怎么被父母骂也还是继续滚个乐此不疲。那个时候耶从来都是随时随地随意大小便,完全不会觉得恶心。这种深层的记忆无法被抹去,就像有些人的爱好,即使被说成变态也不会因此放弃一样。人真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 能吃却不可以吃,可能进行性接触却碰都不想碰,除了“恶心”“可怕”这样的想法在里面之外,与其说这是生理的反应,不如说是我们根深蒂固感情的作用。但是这里说的感情,并不是指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而是人为设定的,换句话说,是一种制度。为什么不会吃宠物呢?不是因为不能吃,而是因为吃宠物这件事是被禁止的。这种“不许吃”的想法被强迫地植入我们的脑子里,渐渐我们就有了“不能吃宠物”这样的感觉。 同时,这也是一个跟文化根基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首先,文化是自然经过加工后的产物。这个被加工过的产物往往让人产生这就是自然的错觉,也就是说我们人为地将自然替换成了被加工后的“第二自然”。而对自然的加工,首先体现在我们对身体的加工上,因为身体是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自然。像是出生时我们自然的发声体系,经过加工后变成了井井有条的音律体系(哼哼唧唧的声音变成了清晰的词句)。而身体自然的运动变成了有序的表情、神态和动作。最容易理解的一个通过操作自然外在而产生改变的例子,就是穿着打扮了。 围着身体打转 对身体表面的加工,除了上述对身体进行象征性的分割之外,还有对身体进行的直接加工。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上,完全没有经过加工的部位基本上不存在。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每天都会梳头、剪发、绑发,画眼线、眉毛,打耳洞,画腮红,涂口红,戴项链、耳环等等。而颈部以下则用布料包裹住,然后涂上指甲油,套上透明的丝袜,穿上鞋子。而对男性来说,身体的大部分基本上都被布料裹住,脸上的功课只在于定期刮胡子。好不容易生长出来的毛发,因为根深蒂几近于强迫的观念又被剃掉。以前的武士总是留有比较极端的发型,就像今天的朋克头一样,在头发上一直做减法。我们每天孜孜不倦地通过变形与加工处理着我们的身体,有时候都想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 让卢·谢弗(JeanloupSieff),《BlackCorset》,年 我们无一例外地深陷身体加工不可自拔,对此法国文化人类学家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vanGennep)说过:“人类的身体就像一块木头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雕刻与造型。可以削掉凸出的部分;可以挖几个洞,让扁平的表面变得栩栩如生。”(《LesRitesdepassage(通过仪礼)》) 通过这样的加工和变形,与生俱来的身体就变得不一样了。在这之中,语言就是最好的证据:由出生时的自由发声,变换到只有有限母音的音律体系,由此诞生了语言。像这种自然的变形是文化的基础。 穿着打扮都是人类对身体加工的行为。衣服在这里起到了复杂的变形作用:利用布料可以创造膨胀、伸展或是纤细、紧绷的感觉,在身体的表面作出不同的文章。 这么看来,人到底为什么会通过穿着打扮来装饰自己呢?人们为什么又会对自己本来的身体感到不满,进而需要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变形呢?而对身体的加工和变形到底又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呢? 注: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vanGennep):-,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他在《LesRitesdepassage(通过仪礼)》的书中首先提出了“分离-边缘-聚合”的“通过仪礼”。通过仪礼,又称人生仪礼。在人一生中经历的几个生活阶段中,其社会属性随之确立。在进入各个阶段时,会有一些特定仪礼作为标志,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评价。 选自《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鹫田清一著吴俊伸译日本服饰与时尚中的身体哲学,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工作中的破、解、离墨语者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宣传公号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