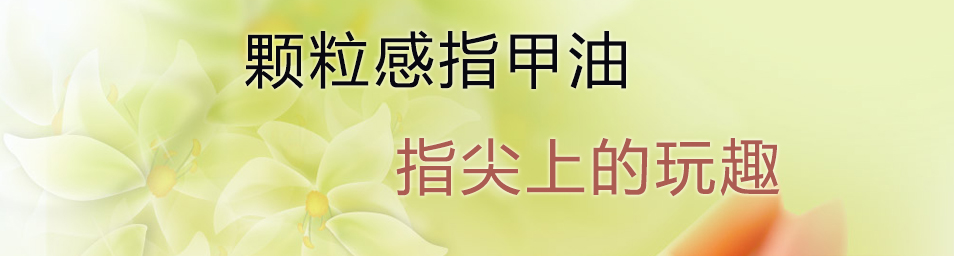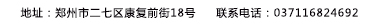|
文︱万征 了个愿 在纽约,有一幢房子特别想看看,它不新也不算旧,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可能有点“过时”。这房子是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年去世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在建筑界可谓是个教父级的人物,他99岁的生命和无尽的创造力为世界建筑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他是年第一届普利茨克建筑奖的得主,早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部任主任一职,曾组织过一场现代建筑展览会,写过一本《国际风格:年以来的建筑》,“国际风格”一词就出自这本书,此书也奠定了他建筑理论家、评论家的地位。他还是密斯·凡·德·罗的超级脑残粉,出资为密斯办展览,宣传密斯的建筑。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密斯合作设计过纽约西格拉姆大厦,密斯风格也影响了他在50、60年代的许多作品。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菲利普·约翰逊突然改变主意了,玩起了新花样,像个叛逆者背离了他一直追崇的现代主义。年设计的纽约电报电话公司大楼,他在高层摩天楼上做了个好似希腊神庙上的三角形山花,并套用了欧洲文艺复兴建筑的某些样式。总之,这房子非同一般,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我读书的时候正是后现代主义建筑风靡之时,像菲利普·约翰逊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 要看这房子并不难,它就在曼哈顿56街。但不知具体位置,得要徒步去找。一个下午,顶着烈日在曼哈顿中城转。我在麦迪逊大道一家麦当劳店喝了一杯苹果汁后出来继续向北走,走到56街的街口处,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正犹豫该往哪边走时,真的,我大约是在0.5秒的时间内便断定应该往右边走,因为我在路口处看到了那个有圆形缺口的三角形山花,几乎是在一瞬间便认出了它,尽管它在林立高楼的中间只露出一只角,一个不完整的小小的角,但我凭这个角确信一定是它。我坚定地向前走去,三角形山花慢慢露出了峥嵘。 走到它跟前的时候你必须要仰着头才能看到顶部那山花,在相对于建筑的高度显得有些狭窄的街道上看不到建筑完整的立面。我站在街对面一家鞋店门口,看着建筑下部足有5、6层楼高的拱形入口,那个巨大的圆拱,骨子里仍是西方古典建筑的精髓。外墙花岗石的颜色在经历多年日晒雨淋后已经有些暗沉、斑驳,但石材砌筑的线条清晰且富有逻辑。呵,一个戏虞的古典主义,是个玩笑?一座调皮的建筑,它曾经是个宣言,试图要调戏一下现代主义的单调乏味。做建筑真的很难,像约翰逊这样精力旺盛的建筑师总是善变,然而,好的建筑却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筛选,我无法评论它,更无法给它下定义,也许几十年、几百年后,自有一番评说。 人们在街道上平静地走过它,没有人多看它一眼。当年的一大建筑事件在今天纽约人眼里仿佛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所在。几辆公共汽车从它面前驶过,一辆敞篷旅游大巴满载着一车戴着墨镜,穿得花花绿绿,手里拿着iphone6的观光客从我面前驶过,一面美国国旗插在一个圆形窗洞上,底层店面有“SONY”的标识,这房子现在不再属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它已被日本索尼公司收购。今天,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久远的故事,除了建筑教科书上那泛黄的几页纸上印着它的图片,人们不再提它。 看到这座房子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在自己对建筑有着无限热情和有限阅读内容的年代知道的仅有几位建筑师中便有这位菲利普·约翰逊先生。看它,算是了个愿。 穿越52街 其实,菲利普·约翰逊也不都设计高层摩天楼,他也设计过小房子,除了他在康涅狄格州的玻璃自宅,在曼哈顿的中城还有一处“城市住宅”。据说它是约翰·洛克菲勒一世夫人的私人会所,里面陈列着她品味不俗的雕塑收藏。它就在52街号,离我住的酒店仅一街之隔。但临出国时的准备工作没做充分,疏忽了一个细节,是在东52街还是在西52街?那房子本是私人的住宅,并没有一个公共的称呼,所以也没法问。呵呵,有点要命,只有挨个去找。 一天下午,回到酒店大约是4点多,时间还比较早,觉得应该去找找。从51街到52街真的是近,2、3分钟便到了。先问了路口一个穿制服的工人,号应该是在东还是在西,回答是,分别都有,也就是东52街有号,西52街也有号。 那就先去西吧。一家一家仔细看,街的这边是单数房号,对面就是双数房号。没有。再往东走,再一家一家看,穿在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号,号……快了,号,号,啊,号,真是它,果然就是它!它就夹在两幢比它高的房子中间。外观封闭,只中间一个小木门,下部是红砖墙,上部是钢和玻璃,走在路上如果不注意,或是根本不知它的来头,会忽略它,因为从外观看它的确很平常。但走到近处,会发现上部黑色钢框和那面红砖墙的精致,门框里的一些小细节,门铃,对讲机,还有门扇上的门锁,以及门扇下部用金属包覆的部分都很用心,知道这不是平庸之作。鼓起勇气按了按门铃,无人应答,再次按了按门铃,里面依然是静悄悄的。低头看见靠近门的地面上飘落着几片树叶,不知里面是否还有人居住,抑或是房子已另移主人? 天色快要暗下来了,太阳在房子的背后慢慢沉下去。这房子在夕阳中更显得宁静。僻静的街道上偶有路人经过,但没有谁像我一样在这房子前驻足观看良久。 你真好看 一天早晨,我乘坐地铁准备向北去上城,去哥伦比亚大学。恰逢上班高峰时间,车厢里挤满了人,坐过了两站到60几街才找到座位。隔着过道,对面座位上一个小姑娘紧盯着我,我注意到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大约有8、9岁,深棕色直发往后梳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辫,白净光洁的皮肤,一双文静深沉的大眼睛,粉绿碎花的连衣裙,一看就觉得不是纽约人。她的身边还有一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小姑娘,估计比她小一点点,看样子有7、8岁,大约是她的妹妹,妹妹不及她漂亮。但两个女孩都很像她们的妈妈,看她们的举止和神态我猜她们是法国人,如果是的话,苏菲·玛索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小姑娘盯着我看,我盯着小姑娘看,然后她笑了,我也笑起来。她们比我提前下车,离开车厢时她又看我一眼。我在心里跟她说了一句:你真好看。 电子阅读器和Girlboss 一次乘地铁去曼哈顿下城,一个大约50多岁的男士坐在我旁边。他是位很有风度的先生,典型的白种人模样。有些花白的金色头发很好看,穿一件洗得很旧的浅蓝色棉布衬衣,和同样洗得发白的卡其色短裤,与浅棕色翻毛皮鞋搭配在一起有种很休闲的味道。手里拿着一台电子阅读器正在阅读,那阅读器显然和中国亚马逊卖的Kindle阅读器不一样,但或许是Kindle的老版本也说不一定,但我很喜欢那种老旧的款式,和他的装束和气质非常搭调。 这位先生的旁边坐了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我之所以称她为女孩,是因为她的确很年轻,可能不到20岁。尽管额头上有些许的青春痘,但肤色很白,头发很黑,嘴唇很红,指甲上也涂上大红色的指甲油,显得格外醒目。她天生长长的睫毛上又刷上了厚厚的睫毛膏,使眼睫毛显得更长更密。她正低头读一本厚厚的纸质书,从她大红色的指甲间看过去,书名是:Girlboss。我有点好奇,大概这是本小说,但也许是那种励志的成功学之类的心灵鸡汤。从她的外貌可以推测她或者她的父母先辈可能来自土耳其、希腊,或是近东的某个国家,但我却无法猜测内心的她怀揣着怎样一个梦想。纽约,的确是一个孕育各种梦想的地方。自我奋斗,白手起家,一切皆有可能,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纽约客至今仍然在延续着这座城市曾经的传统。 Hashbrown(炸土豆饼) 纽约的早餐是个问题。酒店没有早餐,得自行解决。但酒店房间里有冰箱,一般会在超市买些水果、果汁、酸奶、面包之类的食物。但老吃这些也会觉得腻味。一天早上,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换换口味,决定上街去吃。其实可选择的余地非常之小,一,街口卖甜甜圈和咖啡的流动小摊,二,麦当劳,三,自助式快餐店。第一种上次来已经吃过,甜得一塌糊涂,拒绝再吃。第三种其实就是吃些面包、果汁、咖啡、沙拉之类的东西,跟在超市买来拿回酒店房间里吃是一样的。至于第二种就是汉堡包、炸薯条、炸鸡腿的代名词。 但美国的麦当劳餐厅早餐要卖一种叫Hashbrown的炸土豆饼,每天只卖到中午12点。这是将熟土豆捣碎后压制成椭圆形约1厘米厚的饼状,然后再放到油锅里炸,一锅只能炸六个,待炸成金黄色后捞起,一口咬下去香气四溢的油炸饼。有点像中国的糍粑块,只不过不是用糯米而是用土豆做的。1美元一个,不便宜,油炸食品不健康,但偶尔为之也不妨。在酒店后面的50街找到一家麦当劳,进去后便看见几个黑人男子独自闷坐在各处,一声不吭地吃着那经久不变的国际主义食物,吃汉堡包的吃汉堡包,吃炸薯条的吃炸薯条。我买了两个Hashbrown和一杯果汁,找到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吃一边看着街道上那些匆忙的路人。早晨的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到桌子上,刚好照在装Hashbrown的有几点油渍的小小纸袋上。 一场雨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每到一个地方都应该淋一场雨,雨是那个地方的精灵,在雨中可以吸纳这个地方的精气。呵,听起来颇有道理,以后每去一个地方,我都记得这句话,也在意是不是淋了雨。 那天真的很闷热。午后来到纽约大学,慢慢转到华盛顿广场,远远地从一片绿丛中看到广场的大理石拱门,那是为纪念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周年而修建。广场上有很多人在拍照,有些人从拱门下穿过。我站在拱门前定神凝望着它,这时天色突然暗下来,乌云密布,刚用相机拍了两张,顷刻间豆大的雨点便打下来,我迅速朝拱门下跑去。大约3米多深度的拱门下已经站了很多躲雨的人,有旅人,有路人,散步者,学生,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我身边就站着这么一位妈妈,她穿一身粉红色的吊带连衣裙,金发碧眼,婴儿车上的小baby也是金发碧眼,恐怕还不到1岁,孩子惊恐的大哭,婴儿车上挂着很多五颜六色的玩具,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孩子哭一会儿被哄住了,停止了哭声,但过一会儿又开始哭起来。拱门很高,大约有17、18米,所以站在下面依然会淋到雨,大家都打着伞站着。一阵狂风吹来,伞也被吹翻过去,站在靠外面,又没有伞的人便也淋得全身湿透。 大约半小时以后,天色渐渐亮了,雨开始小起来,拱门下的人也开始散去。我离开广场,大约是在第3大道第9街开始一路向北步行,我决定穿越几十条街区回酒店。当快要走到the13Street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且越下越大,大到不能再走,在the15Street找到一处路边的屋檐下躲雨,周围也都是躲雨的人,还有很多人没有伞。 等雨小后再次出发,约莫走到百老汇大街东24街时,磅礴的大雨倾注而下。再次找了街边一处可以躲雨的地方,在一家叫GREGORYSCOFFEE的咖啡店门前的檐廊下。一位穿灰色衬衣的印度男子从我身边急步而过,街面上无数黄色出租车飞驰向前,一辆车身上印着戴墨镜的詹姆斯·邦德剧照的大幅广告的公共汽车缓慢地向北前行,黑色的警车闪着警灯就停在檐廊的前面,大雨迅速汇集在街边的下水道口形成一股急流。 灰暗的天空下,路灯亮起,街对面商店的灯光也显得格外明亮。雨稀里哗啦地下着,我倒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开始欣赏起街道对面建筑那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立面,那转角处巨大的拱门,那窗檐上雕刻的装饰,再看看自己脚下,我的鞋已经灌满了雨水,早已湿透了。 对不起,需要预约 一个阴暗的下午,曼哈顿第三大道,东6街,CooperSquare,库珀广场。一幢扭曲的金属、玻璃和混凝土外墙的房子在沉郁的天空下闪着银光,仿佛顷刻间将要崩塌,在下城那些规矩端正的传统红砖房子中间显得格外突出。库珀联盟学院科学与艺术大楼,在这片区域是如此的不协调,好像一个恶作剧般搞怪,戏弄了街对面那幢有拱券和柱式的老库珀联盟学院大楼,诙谐、幽默,还有几分顽皮。建筑师汤姆·梅恩,年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其建筑风格颇有些像弗兰克·盖里,有些张狂,有些反主流,有着创造性的能量。 几根粗壮、歪斜的混凝土柱临街而立,而临街的道路正在施工,用橙色栏杆围起来,几个穿黄色外套的工人正在场地内操作着机器。从一侧一个圆形旋转门进去,左侧一个下沉空间里面正展示着很多平面设计作品,海报、书籍、图形……这是一个设计学院。径直往前走,在素混凝土的空间里有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旁是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楼梯通向上面的楼层,楼梯口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粗条钢构网架,限定出一个颇有气势的入口。我问柜台后面一位坐着的黑人男子:“Excuseme,I′mavisiter.CanIvisitthisbuilding?”(劳驾,我是一位访客,我可以参观这座房子吗?)在有些昏暗的室内,他耸了耸肩,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道:“No,I′msorry.Youneedtomakeanappointmentinadvance.”(对不起,你需要提前预约。) ? Excuseme(劳驾) 美国人特别爱说“Excuseme”,什么时候都说。有一天我在第七大道上行走,眼睛看着远处,没注意近处的动静。稍显拥挤的街道上迎面一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男子突然朝我急匆匆走来,他可能有什么急事。当他将要靠近我时差点和我相撞,他立刻止住脚步,由于速度的惯性他的上身有些前倾地扑向我,身材高大的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神情有些紧张和不安,然后轻盈地侧身从我面前走过,我并没有和他相撞,但我听见他嘴里非常小声地说了句:“Excuseme”,非常非常小声,小声得几乎听不见。 …… 一天,正午炙热的太阳照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上空。我在伯纳德·屈米设计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外面,正透过那面玻璃幕墙看里面那些坡道。在门厅问了坐在咨询台后面那位黑人男子,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这房子,回答说因为要刷卡,所以只有持卡的本校学生才能进去。遗憾,那就在外面看看吧。离幕墙约60公分的距离有一道木质栏杆,我站在栏杆内侧往里探望,拿着相机拍照,这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很稚嫩的童声:“Ex-cuse-me”(劳驾),我转过身,旁边站着一个仅有栏杆那么高的白人小男孩,大约3岁,金发,一身蓝色衣裤,白色运动鞋,阳光太强,他眯缝着眼睛,有几分骄傲又有几分认真地看着我。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似乎是挡住了他的去路,又或许是他对我充满好奇。好吧,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我会心地看着他一笑,同样对他说了一声:“Excuseme.” ? 没翅的鱼 “水煮鱼,鱼香茄子,蒜炒空心菜,青菜豆腐汤。”我对站在餐桌边的服务生用中文说道,我一边点菜,他一边在本子上记下菜名。点菜的功夫,我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不远处的邻座一位眼熟的某知名中国艺术家正和他的一帮中国朋友谈笑风生。瞬间时空变换,仿佛不是在纽约,而是在四川,在家门口。 那天晚上,在曼哈顿中城闲逛,找吃的,想找家中餐馆,在纽约待了几天自然就会想到重口味的川菜。从列克星顿大道向东走,在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东53街,找到这家叫“麻辣东村”的川菜馆。 翻看菜单,竟然是如此的齐全,夫妻肺片、红油肚丝、口水鸡、川北凉粉、川式腊味拼盘、老妈蹄花、钟水饺、红油抄手、麻婆豆腐、眉山牛肉、锅盔回锅肉、蚂蚁上树、火爆腰花……应有尽有,都是那些家常的味道。点完菜我又补充道:“水煮鱼要麻辣点。”好像对味道有点不放心。 很快,大约过了十几二十分钟菜便端上来。水煮鱼用一个青花图案的陶瓷大钵钵盛着,面上浮着一层红色的辣椒和油,还在哧哧的冒着油泡。用筷子夹起一块尝了尝,烫嘴,麻辣,鲜香,是四川的味道,形色味俱全。在纽约居然还能吃到如此正宗的川菜,有点喜出望外的感觉。吃完还有店家免费赠送的一人一份的醪糟小汤圆甜品,结账一共是38.6美元。结完账店家照例发给每位客人一个小蛋卷盒子(华人餐馆都会在餐后发这样一种小赠品),打开一看,小纸条上写着:Yourabilitytolovewillhelpachildinneed.(你的爱的能力将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此时,我身边就站着一个孩子,我读高中的女儿,我一直都在帮助她。这话说得好,也等于没说。总之,这是一顿圆满的晚餐。 后来想起这顿饭,想起吃的那道水煮鱼,我问我家孩子,那天在麻辣东村吃的鱼是什么鱼啊?我怎么觉得那鱼没有翅呢? 男孩们 炮台公园,曼哈顿岛最南端,毗邻下城繁华金融区的一片世外桃源,隔哈德逊河可以眺望远处爱丽丝岛和自由岛上的缩成一个小点点的自由女神像。面河的东岸纪念碑,一面面的石墙巍然矗立,石墙上刻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西洋牺牲的四千多名士兵的名字、军阶,以及州别。一个“自由女神像”从我身边走过,码头处,又见一个“自由女神”一动不动地任游客跟他一起拍照。河边的轮渡前挤满了排队等候上船的游客,他们将要去往自由岛,一睹真正的自由女神的尊容。 我坐在一片树荫下的沙地上,几个条形的坐凳围成一个圆形场地。中间有一个供娱乐的音乐装置,表层是一块块有弹性的不锈钢片,当人踩在上面时会发出悦耳的七声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而脚踩的轻重决定了声音的强弱。几个男孩正踩在上面不停地蹦跳,声音响个不停,他们的家长就跟我一样坐在周围的长凳上。过了一会儿,孩子们一个一个上来踩,先是一个黑人孩子,很矮小,约有4、5岁,穿了件红色的T恤衫,蓝色的短裤,白色的运动鞋,声音有力而富有节奏;接下来是一个白种男孩,金发,瘦高的个子,可能有11、12岁,有些腼腆,声音有些羞涩迟疑;下面一个是位黑发、棕色皮肤的孩子,估计有7、8岁,大约是穆斯林阿拉伯人,有些恶作剧似的乱跳,钢片也发出奇怪的噪音,孩子觉得很高兴,毕竟出了风头,他的母亲穿着一身阿拉伯妇女的服装,包着头一声不吭地静坐一边;一个穿背心的东方面孔的男孩上来,约6、7岁,他很规矩,一下一下地踩,声音也一下一下的响,他不太放得开,他的母亲在跟他说着什么,是日语,估计在说叫他大胆一点;另一个东方面孔的男孩上来,好像一开始就很有想法,要踩出一首曲子似的很有步调地踩,小心地踩。过了一会儿便是满头大汗,母亲过来给他擦汗,然后她用我听得懂的汉语跟男孩说:“好了好了,咱们走吧。爸爸在那边等我们呢。” (未完待续) 初稿于年10月9日 定稿于年12月7日 万征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教授 从事建筑空间环境艺术设计教学及研究 文字专注于建筑、艺术及设计 与您分享阅读、旅行和写作 文章及图片版权归本文作者所有,转载须征得作者同意 谢谢合作 ce 赞赏 |